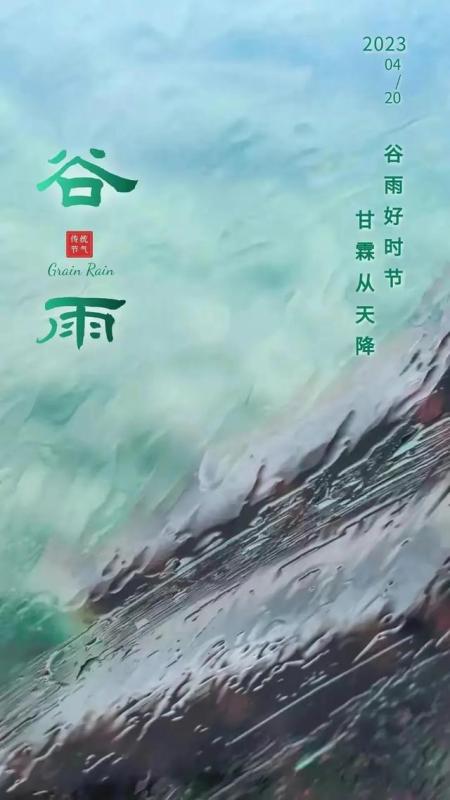“小年”已至,大年不遠,再過七天就是年。
周邊的世界,看上去一如往常;人們的生活,沒有明顯的異樣;過年的味道不濃,人們過年的心氣也不似從前那樣盛騰。
好多人都說,現在的年味兒淡了。
愈是感覺寡淡,愈是懷念從前。
從前的年是何等的令人神往?又是何等的熱鬧?
小時候家鄉過年的情形不知不覺就到了眼前,密密匝匝地展演開來。
“進了臘月門,先生不打人”“小孩兒小孩兒你別饞,過了臘八就是年”,單是從這些民謠里就能感受到快要過年的人們跟往常明擺著不是一個心氣兒。
記得小時候,進了臘月門,平日里做夢都盼著過年的我此刻被肚里的饞蟲攪得更是“度日如年”,天天掰著手指頭算還剩幾天過年,有的孩子為了讓年早一點到來,居然偷偷撕家里的日歷,得猴急到啥程度。
大人們雖不似小孩子這般沉不住氣,可也早早地算計著過年的一切,稱多少肉、買哪些菜、扯幾塊布料、做幾雙新鞋、蒸幾鍋饅頭、買多少爆仗?等等,識字的隨便拿過一張廢紙來記在上面,不識字的直接裝到心里,一天到晚不知掰扯多少回。
計劃再多,大人們也不會一股腦兒地付諸實施,而是按著祖上千百年傳下來的習俗,慢條斯理、有條不紊地進行著。臘月初八熬臘八粥、腌臘八蒜。過了臘月初十,開始隔三差五這里那里地趕集買年貨。逢到周邊集市開集,套上牲口拉著車,載著一家老小,或騎著自行車前馱孩子后馱媳婦,緊趕慢趕去趕集。
四面八方的鄉親們都往一個集市上趕,通往集市的馬路上是一年里除農忙季節外最熱鬧的時光,馬車、驢車、牛車、自行車,隨處可見,趕牲口的吆喝聲、大人孩子的說笑聲、自行車的鈴鐺聲,匯成寒冬里最美的交響,訴說著即將迎春的喜悅。
到了集市上更是熱鬧。肉攤、菜攤、干貨攤、水產攤、布料攤、年畫攤,分列街道兩旁和中央,這些攤子分門別類挨在一起、排成一串,成三路縱隊向遠方伸去,長長的集市一眼望不到頭,琳瑯滿目的年貨晃得人眼花繚亂。
為著人們的安全考慮,爆仗市總是被單獨安排在集市的一頭,離開其他攤子一段距離。那時,爆仗是所有男孩的最愛,我當然不會例外。每次去買爆仗的時候,我總是被爹緊緊地抓著手牽著在人山人海中艱難地穿行,生怕一不小心就被擠丟了。
一路上,被來來往往的人群擠得東倒西歪,滿耳朵都是此起彼伏的叫賣聲、討價還價聲、震天的鞭炮聲,簡直能把腦殼吵成一鍋漿糊,懵懵的。
無論多擠多累,買完年貨滿載而歸,無論大人還是孩子,都是滿臉的喜氣,大人有大人的滿足,小孩有小孩的喜悅。
斷斷續續趕幾個集,年貨備齊了,小年(臘月廿三)也到了。從此,人們開始進入每天都有事做的狀態:祭灶神,掃房子、燉豬肉、煎藕合、炸丸子、蒸饅頭......小年后的七天里,家家飄肉味、戶戶聞油香,空氣中到處都彌漫著過年的味道。
年味就這樣被大人們忙活得越來越濃了!
忙忙活活,轉眼就到了年三十。一早,到祖墳上請回列祖列宗,晚上,滿村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抱著柴火、拎著爆仗、舉著長竿擁到大街上點篝火、放鞭炮。
一堆一堆的篝火熊熊地燃燒著,照亮了夜空,也照亮了人們對新的一年的希冀。
一掛一掛的爆仗接二連三地炸響,炸出了人們心中的喜悅,也炸走了窮氣和晦氣。
篝火、爆仗,將年味推向了最高潮。
著完篝火、放完爆仗,各自回家,守著老的、看著小的,喝著過年酒、吃著年夜飯,享不盡的天倫樂,道不盡的幸福感。
年三十的夜顯得格外短。記得那時,總是剛鉆到被窩里迷糊一會兒,就被爹娘拽起來,跟著爹娘上供、點篝火、放爆仗、發天地馬子,然后吃餃子,吃完趕緊洗臉洗頭換新衣,準備出門拜年去。
有的鄉親能一宿不睡,天剛蒙蒙亮就串門拜年,過年的心氣得有多足,精神頭得有多大?!
初一大拜年,初二開始走親戚拜年,一走走到正月初十開外。走親戚拜年都是家里大人事先給計劃好的,今天去哪兒,明天去哪兒,七大姑八大姨,只要沾親帶故,早早晚晚都要打發孩子到親戚門上拜年。禮尚往來,親戚那邊亦要打發自己的孩子過來拜年。雙方你來我往,你待我待,你親我親,濃濃的親情在人們心中流淌著、蕩漾著。
親戚剛剛走遍,正月十五又到,又是一番熱鬧。
鄉下元宵節沒有燈會,可鬧秧歌遠比燈會熱鬧。
鬧秧歌是鄉下迎新春、過大年、鬧元宵最普遍的文化習俗。那時,村村辦秧歌,年年鬧秧歌,男女老少扭秧歌,實在扭不動的也要去看秧歌。
打從初一開始,逢到傍晚時分,響亮的鑼鼓敲起來,歡快的秧歌扭起來,初十前后開始應邀到周邊村莊巡演(家鄉稱為“聯燈”)。從正月初一直扭到十五晚上才“謝燈”(謝幕)。
至此,過年算告一個段落,但還沒有結束,因為正月二十五要“打囤”(又稱“填倉節”),二月二又是“龍抬頭”的日子,所以民間向有“不出正月就是年”的說法。
出了正月門,人們的心才真正靜下來,開始新一年的勞作。
現在過年與以往大不一樣。
如果說,過去是以牛車、自行車為代表的慢生活,現在則是以汽車、高鐵為代表的快節奏。
一切都在加快,尤其是對于我們這些出門在外的人,過年的時間大大縮短,公職人員七天假,外出打工經商的最多也不過十來天。
過年的那些流程和習俗只能由留守在家的老人去操辦,我們千里萬里趕回家的目的只有一個,陪著老人過最核心的“年”。
留守在家的老人如今對過年的念想也跟往常不一樣,不再是對物質的欲念,而是對兒女歸來團聚的渴盼。
秧歌依舊在鬧,可鬧秧歌的村和人比之當年少了很多。年輕人早早地回城去了,只剩下一些上了年紀的老人、孩子鬧秧歌,跑不起來、蹦不起來、跳不起來,少了人頭攢動的人氣,少了生龍活虎的活力,也少了各種花樣,只能跟著鼓點扭一扭地秧歌罷了。
好不容易回家一趟的年輕人走親戚拜年不能像往常那樣一家一家沉著氣地挨著走了,受時間所限,至親一天串幾家點個卯,遠一些的親戚就算了。一來二去的,一些遠方親戚就斷了。
......
時代如上漲的江水,過往與現在被悄無聲息地分割到了兩岸,愈來愈遠。
回望對岸,那里珍藏著我們那貧窮而又歡樂的童年。
此時此刻,我們正站在當年做夢都想又不敢想的岸邊。
兩相對比細思量,當年的年味為何而濃如今的年味因何而淡?
從前的過年,人們是用一個月的享樂和團聚來犒賞一年日夜不停的辛勞,彌補一年在外打拼的離愁。
從前的美好,是基于生活貧窮而生出的無限渴望,是基于文化匱乏而創造的無限歡樂,是基于極度短缺而導致的稍有改善便無限的滿足。
而今的過年,時間就是金錢,人們不可能再悠閑自得地享樂一個冬天,不可能再悠游自在、有條不紊地鋪排著過年。游子回家更多為的是血濃于水的親情和那長留心中的儀式感。
而今的淡化,是物質文化生活的極大豐富降低了人們對傳統美食的執念和對傳統文藝的追捧,是交通的便利、通訊的發達緩解了父母子女彼此間的思念。
然而,無論時代如何發展,生活如何變遷,過年這一傳統習俗的“魂”不會丟,人們心中的“根”不會斷。無論“年”有多么短暫,無論走得多么遙遠,爹娘在哪里,老家在哪里,兄弟姐妹在哪里,父老鄉親在哪里,哪里就是根脈所在,哪里就是團聚之地、哪里就能一解離愁,哪里就有無盡的歡樂與溫暖。
無論濃與不濃,年都在那里,循回往復;
無論淡與不淡,根都在那里,不離不棄;
無論天涯海角,情都在那里,始終不渝。
現在,讓我們停下忙碌的腳步,準備回家過大年!
最后,恭祝各位新春愉快,闔家幸福、萬事如意!
(壹點號 魯北往事)

本文內容由壹點號作者發布,不代表齊魯壹點立場。
, 以上就是魯北人小,魯北往事小年話的內容,下面小編又整理了網友對魯北人小,魯北往事小年話相關的問題解答,希望可以幫到你。
民國軍閥韓復榘,真的是“山村野夫”嗎?有哪些關于他的民間段子?
大明湖 ,明湖大,大明湖里有荷花; 荷花上面有蛤蟆,一戳一蹦達。 不知道大明湖畔的夏雨荷讀了這首小詩后會作何感想。 在我看來,這首風格奇特的小詩畫面感很強。
山東人闖關東的時候選擇的路線是怎樣的?
闖關東是東北老人們常提起的話題,現在東北三省很大的一部分人,是從關內闖關東過來的,都是關內的后代,東北的漢子耿直,好爽,勇敢,講義氣,遺傳了山東人的基。 山東。
你的心里是否有想說卻又不敢說出的秘密?
愛你,是我心里想對你說,卻不能說出口的秘密…… 或許每個人心里,都藏著一個不能說出口的秘密……而最讓人心酸的秘密,就是“愛你”是我不能對你說出口的秘密。
梁希森的人物經歷?
史前檔案:包工頭出身,1999年入主北京玫瑰園,自此在地產界一炮走紅。 梁希森幼年曾一度以討飯為生,早年做過鐵匠,并在面粉廠、裝修隊做過工人。1992年,他組。
以前用鐮刀收割小麥都是早上幾點去的?你懷念用鐮刀收割小麥的時光嗎?
記得很清晰,那時還在讀小學、初中,只是高中時到了縣城讀書,就很少參加家里的麥收了。 那時的假期還有麥假,二周的時間! 爸媽都是起的很早,具體不清楚幾點,。 記。
三國時期的“劉升之”到底是何人?
有人認為劉升之是劉禪別名,另一說是劉備別子。 先說劉禪 《三國志.魏書.明帝紀》注引《魏略》載明帝時期的公文:“劉升之兄弟守空城而已” 根據《魏略》,劉。 第。
等你老了,是喜歡城里生活,還是喜歡鄉下生活?
等自己老了,是喜歡城市的生活,還是覺得喜歡鄉村的生活?城市有豐富多彩的生活,繁華興旺發達的地方,熱情洋溢,交通便利,四通八達,風光秀麗,高樓立林,環境。 我拎著。
現在農村的年輕人是不是不會耕田種地了?
現在的年輕人是不是不會耕田種地了。現在農村有些地方土地稀少,一個家庭用不了全部在家種地,本身家里土地少,一個人在家種地完全應付得了,結果就出現了年輕在。
70后60后你們小時候生活是怎樣的,大家都來說說?
60,70后小時候,大都很窮。 過著集體生活。每個家庭里小孩七八個,十來個也很正常。衣服,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過給老三。破了再補,縫上繼續穿。直到沒法穿。 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