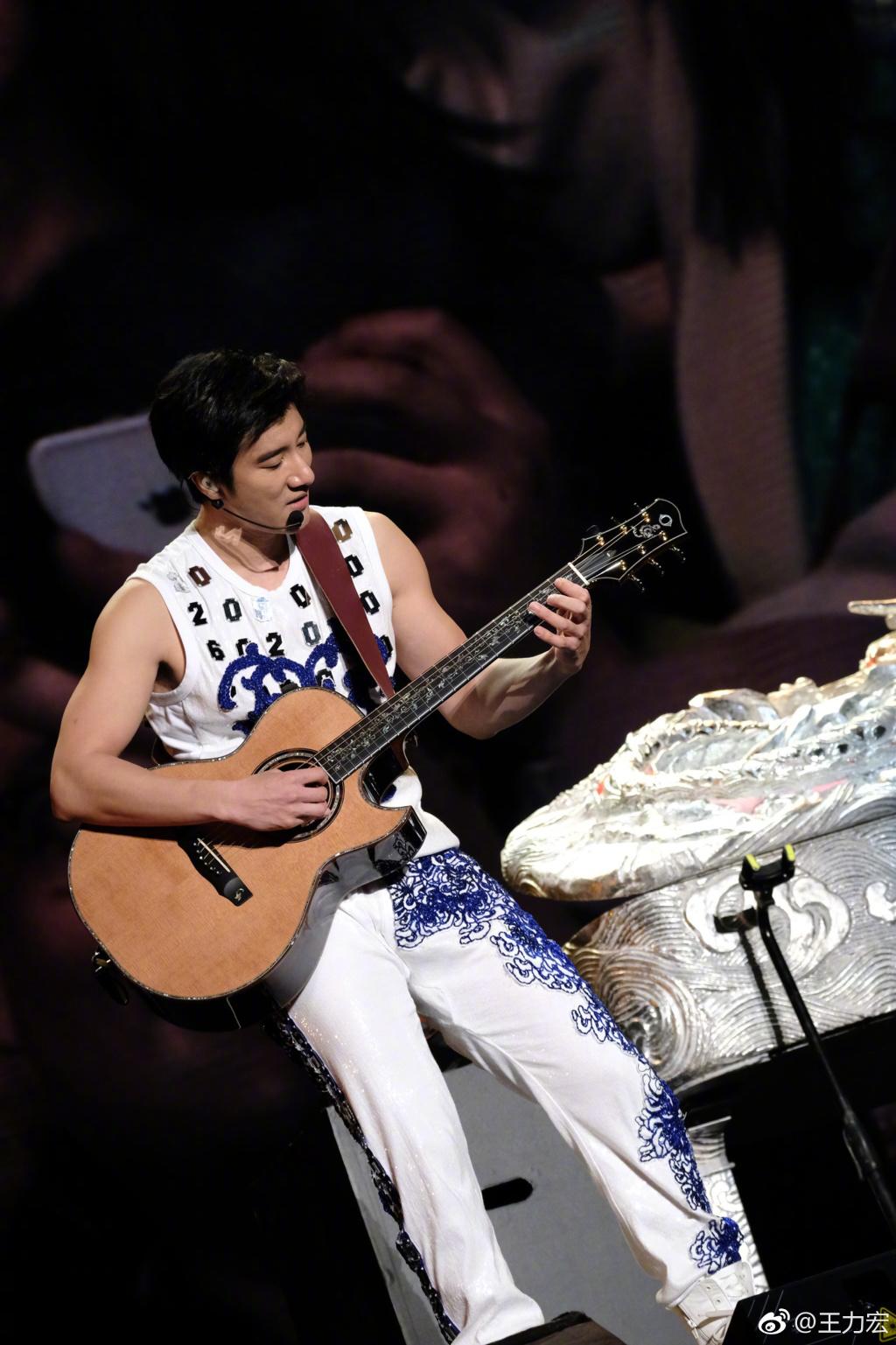原子彈加速了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而原子能的威力也逐漸引起了思想家的擔憂。清華大學著名教授潘光旦在《觀察》周刊第二期上發文,論述人與物的關系、以及人對自身的控制能力的思考。

清華大學教授潘光旦
人的控制與物的控制
潘光旦
中國有句老話,說,童子操刀,其傷實多。這句話恰好形容了三百年來科學進步的一半的結果。刀是一種人所發明的工具,本身無所謂好壞,只是用途有好壞,用得適當就好,不適當就壞。刀自身不能發揮它的功用,發揮它功用的是人,而人卻有好壞之分,有適當不適當或健全不健全之分。以適當而健全的人來利用一種工具,其功用或結果大概也是適當、健全、而有益的;否則是有害的。童子操刀,指的是后一種的可能的功用。大凡人利用事物,全都得用這眼光來看。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自然的事物如此;人所自造的文物,包括一切比較具體的工具制作與比較抽象的典則制度在內,尤其是如此。說『尤其』,正因為它們是人造的,是人的聰明的產物,如果控制無方,運用失當,以至于貽禍人群,那責任自然更較嚴重;人的聰明能產生這些,而竟不能適當的控制運用這些,至于尾大不掉,自貽伊戚,也適足以證明那聰明畢竟是有限罷了。
我們也得用這種眼光來看科學,科學也正復是一種人造的工具,一點也不少,一點也不多。它本身也無所謂好壞,好壞系于人的如何控制運用。一部分人,見到科學昌明以后,人類的一部分獲取了種種利用厚生的好處,于是就贊揚科學,歌頌科學,對科學五體投地,認為是人類的福星。我想除非一部分人中間,有人生就的是一副詩人性格,動不動要發抒他的感傷主義,這是大可以不必的。另一部分人,見到在同時期以內,科學表現了不少的摧殺敗壞的力量,特別是在歷次的大小戰爭里,于是就批評它,詛咒它,認為人類遲早不免因為它而歸于寂滅。而自原子能的發明以后,這末日可能來臨的很早;我認為這也是一種感傷主義的表示,大可以不必的。

我們要認清楚,一切問題的癥結在人,關鍵在人。童子操刀,問題絕對的不在『刀』,而在『童子操』。人運用科學,問題也決不在科學,而在人的運用與運用的人。我們要問這運用科學的人是不是真能善于運用,真有運用的資格。換一種問法,就是他配不配運用。所謂善,所謂有資格,所謂配,指的是兩層相連的意思:一是他在運用之際,能隨再參考到人群的福利,始終以人群福利為依歸;二是他,運用者自己,必須是一個身心比較健全的人,至少要健全到一個程度,足以教他實行這種參考,篤守這個依歸。這兩層意思,第一層指人的運用,重在運用;第二層指運用的人,重在人。
我指出這兩層意思的分別來,因為『人』與『運用』之間,比較基本的終究是人,人而健全,運用是沒有不得當的,反過來就很難想像了。而近年以來,中外論者鑒于科學對人群的利害參半,對于有害的一半總說是『運用失當』,難得有人更進而提出如下的一類問題:失當的原因究竟何在?此種失當是偶然的呢,是一時計慮的錯誤而可以避免的呢,還是有些基本的因素教他不得不發生而隨時可以發生的呢?這基本的因素里可能不可能包括人自己?可能不可能人本身就不適當,因而他對于科學的運用也就無法適當?好比騎馬,馬是工具,人是馬的駕駛者,騎馬之人雖未嘗不聰明靈活,未嘗不略知駕駛之術,但也許年事太輕,或適逢酒后病后,神志不夠清楚,終于把馬趕進了一個絕境,造成了斷頭折足的慘劇。這又回到童子操刀的比喻了。然則問題還不在一個操字,而在童子本身。
童子操刀,最淺見而感情用事的人責備著刀。其次也只是在操字上做功夫,總說操得不得法,誠能操之得法,問題就解決了。一九三一年二月,愛因斯坦在加利福尼亞州工科學院對學生作公開演講,說,『光輝燦爛的應用科學既算省了工作的時間,減輕了生活的負擔,而對于人類幸福的促進,又何以如是其少呢?我們簡單的答復是:我們還沒有學到致用之道,一些明白事理的致用之道。要你們的工作得以增加人類的福佑,只是了解應用科學是不夠的。你們得同時關切到人。人的自身與人的命運必須始終成為一切技工的努力的主要興趣。在你們繪制圖表與計算公式的時候,隨時不要忘記這一點。』這一番話是不錯的。從愛氏的嘴里說出來,自然更有分量;但是不夠,單單就「操」字上找答復,而不就童子身上找答復,所以不夠。愛氏在這話里,也似乎只見到『人的運用』,而沒有見到『運用的人』。要見到了運用的人,問題才搔到了癢處。
三百年來,物的研究認識,物的控制運用,誠然是到了家,到最近原子能的發見與原子彈的實驗成功,此種認識與控制更是將近登峰造極。但人自己如何?人認識自己么?人更進而控制自己么?我們的答復是,人既不認識自己,更不知所以控制自己。人自己也是一種物體,這物體是一個機械體也罷,是一個有機體也罷,它總是一個極復雜的力的系統。我們對于這力的系統,根據物有本末事有先后之理,我們原應先有一番清切的了解,先作一番有效的控制。但三百年來,科學盡管發達,技術盡管昌明,卻并沒發達昌明到人的身上來,即雖或偶然涉獵及之,不是迂闊不切,便是破碎支離。結果是,我們窺見了宇宙的底蘊,卻認不得自己;我們駕馭了原子中間的力量,卻控制不了自己的七情六欲;我們夸著大口說『征服』了自然,卻管理不了自己的行為,把握不住自己的命運。這正合著好像是耶穌講的一句話,我們吞并了全世界,卻是拋撇了自己的靈魂。比起這句話來,上文童子操刀、醉漢騎馬一類的話,還算是輕描淡寫的。

人至今沒有適當的與充分的成為科學研究的對象,是很顯明的。人屬于一個三不管的地帶:
第一、人雖然也是一種生物,并且是一種動物,但生物學與動物學不管,至少是不大管,或雖管而其管法和一棵樹、一個蟲、一只青蛙的管法沒有分別,即雖管而于人之所以為人不能有所發明。
第二、人類學與社會學,以至于其他種類社會科學都算是以人做對象的科學了;但說來可憐,這對象是有名無實的。這些學問只是在人身外圍兜著圈子,像走馬燈中走馬之于蠟燭一般。體質人類學算是最接近的,但它的注意范圍很有限,除了活人的那一個皮囊,叫做形態的,和死人的那一副架子,叫做骨骼的,以及這兩件事物在各種族中間的比較而外,也就說不上多少了,試問我們認識了這個皮囊和掛皮囊的架子,我們就算認識了人么?所謂文化人類學,名為研究文化的人,實際是研究了人的文化,名為是研究產生者,實際是研究了產物,至多也只是牽涉到一些產生者和產物的關系,以及產物對于產生者的一些反響;至于產生者本身究屬是甚么一回事,我們的認識并沒有因文化人類學者的努力而增加多少。社會學是人倫關系之學,似乎所重在關系的研究,而不在此種關系所從建立的人。社會學的對象是人倫之際,要緊的是那一個際字,好比哲學的一部分的對象是天人之際一般,所以在不大能運用抽象的腦筋的學子往往不免撲一個空。所撲的既然是一個空,不用說具體的人是撲不著的了。經濟學原應該一面研究物力,一面研究人欲,然后進而研究物力與人欲的內外應合,兩相調適;但截至目前為止,無論是正統派的經濟學,或唯物論的經濟學,似乎始終全神貫注在人身以外的物力的生產與支配之上,而于人欲的應如何調遣裁節,完全恝置不問。物力有限,而人欲無窮,以有限應無窮,前途必有坐困的一日,即行將來臨的原子能時代恐也不成例外;而不幸的是,問題中那無窮的一半恰好就是經濟學所『無視』的一半。政治學與法律學都是所謂管理眾人的學術,而它們所講求的管理方法都是甲如何管理乙,張三如何管理李四,而不是甲與乙,張三與李四,如何各自管理自己,或于管理別人之前,先知所以管理自己。總之,各門社會科學犯著一個通病,就是忘本逐末,舍近求遠,趨虛避實,放棄了核心而專務外圍。所謂本、近、實、與核心,指的當然是人物之際的人、和人我之際的每一個人的自己而言。這邊是三不管中的第二不管。
第三,人體生理學、心理學、醫學、一類的科學在人的研究上我們承認是進了一步。它們進入了人身。上文所說的那種通病它們并沒有犯,我們不能說它們『迂闊不切』。它們犯的是另一種通病,就是上面也提到過的『支離破碎』。分析的方法原是三百年來一切研究具體事物的科學的不二法門。名為分析與綜合并行,實際所做的幾乎全部是分析工作。但分析就是割裂,割裂的結果是支離破碎,這在人以外的物經得起,人自己卻經不起,死人經得起,活人卻經不起。無論經得起經不起,支離破碎的研究,零星片段的認識,等于未研究,不認識;因為人是囫圇的,整個的,并且是個別的囫圇的或整個的,而零星片段的拼湊總和并不等于整個。總之,截至最近幾年為止,即在這些直接應付人的科學里,人也未嘗不落空。我說截止至最近幾年,因為一部分生理學家、病理學家,特別是精神病理學家,年來已經充分看到這一點,認為有機體是不容分解的,人格是不容割裂的,而正在改換他們的研究方法中;但時間既短,成就自然有限。
總上三不管的議論,可知人類自己對于人之所以為人,每一個人自己對于我之所以為我,至今依然在一個『無知』與『不學』的狀態中。『不學』的下文是『無術』,就是,既不認識自己,便無從控制與管理自己。人不能管制自身,而但知管制物,其為管制必然是一種胡亂的管制;人對于自身系統中的力,不知善用,對于其意志、理智、情緒、興趣、欲望、不知如何調度裁節,而但知支配運用身外的種種物質系統中的力,其為運用必然是一種濫用。濫用的結果是『傷人實多』,而這個『人』字最后不免包括濫用者自己。這在上文已經預先籠統說過,但至此我們更可以說得明細一些。

人對自身的認識與控制是一種尚待展開的努力。此種努力分兩層。一是就整個屬類言之的。人也是物類的一種,但究屬與一般的物類不同,他有他的很顯著的特殊性,惟其特殊,所以研究的方法與控制的技術勢必和其他的物類不能一樣。上文囫圇或整個之論便是屬于研究一方面的。至于控制,即就此人控制彼人而言,我們就不適用所謂『集中』『清算』或『液體化』一類的方式,這些都是把適用于一般物質的概念與方式強制的適用到人,此其為適用也顯然的是一種不認識人的濫用。不過更重要的是第二層。人是比較唯一有個性而能自作主張的動物;也正唯如此,我們才產生了關系復雜的社會與制作豐富的文化。每一個人是一個有機體,每一個人是囫圇的,而其所以為有機,所以成為囫圇,每一個人又和每一個別的人不一樣。這樣,研究與控制的方式便又須另換一路;即事實上必須每一個人各自研究自己,方才清楚,各自控制自己,方才有效,別人根本無法越俎代謀;別人有理由越俎代謀的,在任何人口之中,只是絕少數的智能不足和精神有病的人。
所以真正的人的學術包括每一個人的自我認識與自我控制,舍此一切是迂闊不切的,支離破碎的,或是由別人越俎代謀而自外強制的。前人的經驗,無論中外,其實早就看到這一層道理,所謂『自知者明,自勝者強』的即是。不過看到是一事,做到又是一事,以前雖也有大致做到的賢哲,但總屬少數,今后人的學術的任務,我以為就在更清楚的闡明此種方法,更切實更精細的講求它的做法,而此種學術上的任務也就是教育的最基本的任務。目前的學術與教育是已經把人忘記得一干二凈的。學不為己而為別人,是錯誤,學不為人而為物,是錯誤之尤,目前該是糾正這大錯的時機了。
有了明能自知與強能自勝的個人,我們才有希望造成一個真正的社會。健全的社會意識由此產生,適當的團體控制由此樹立;否則一切是虛設的,是似是而非的,意識的產生必然的是由于宣傳,而不由于教育,由于暗示力的被人漁獵,而不由于智、情、意的自我啟發;而控制機構的樹立也必然是一種利用權力而自外強制的東西。這又說著當代文明人類的一大危機了。一般人不能各自控制自己,有欲望而不知善自裁節,有恐怖而不知擅自鎮懾,有憂慮而不知善自排遣,有疑難而不知善自解決,于是有野心家出,就其應裁節處加以欺誑的滿足,應鎮攝與排遣處,一面加以實際的煽揚恫嚇而一面加以空虛的慰藉護持……;野心家更一面利用宣傳的暗示,一面依憑暴力的挾持,于是一國之人就俯首帖耳的入了他的掌握,成為被控制者,成為奴隸;其間絕少數稍稍能自立的,即自作控制的,亦必終于因暴力的挾持而遭受禁錮、驅逐、以至于屠殺。獨裁政治和集權政治不就是這樣產生的么。希特勒墨索里尼一類的天罡星不就是這樣應運而下凡的么?
什么是野心家?從本文的立場看,野心家就是最不能控制自己而不幸的又有一些聰明才干足以助紂為虐的人。野心家的野即應作如是解釋,自己不能控制以至別人也不容易控制他,就是野。希特勒有種種欲望,其中最大的是愛權柄的欲望。他自己不知所以運用意志的力量來控制這欲望,反而無窮盡的施展出來,一任這欲望成為控制他人的力量,控制得愈多,他的權柄便見得愈大,控制了德國不夠,更進而控制東歐,全歐,以至于全世界。有一個笑話不是說希特勒拜訪上帝,上帝不敢起來送行,深怕他一站起來,離開寶座,希特勒就要不客氣的取而代之么?這真十足描寫了野心家愛權若狂而不知裁節的心理。不過從控制德國以至于全世界,但憑欲望是不夠的,他必須運用物力,必須駕馭科學,規模之大,又必須和他的欲望相配合,于是他就從人的控制進入了物的控制,從人力的濫用進入了物力的濫用,而就當時德國與其鄰邦的形勢而論,因為大部分直接運用物力的人,例如科學家之類,向來沒有講求過自我控制,自作主張,也就服服帖帖的由他擺布,受他驅策,至于肝腦涂地而不悟。第二次世界大戰,一部分所由演成的因緣不就是這樣的么?

禍福無門,唯人所召;文明人類一大部分的禍患,我們可以武斷的說,是由于人自己釀成的,而其所由釀成的最大原因,是自我控制的不講求與缺乏。這種局勢是自古已然,于今為烈;而今日所以加烈的緣故,則坐一面人自控制的力量既沒有增加,甚或需有減削,而人對于物力的控制的力量,則因科學的發達而突飛猛進。兩種力量之間,產生了一個不可以道里計的距離。社會學家稱此種不能協力進行的現象為『拖宕』,拖宕一名詞是何等的輕淡,而其所釀成的殃禍卻真是再嚴重沒有。不過這種嚴重的程度,一直要到第二次大戰將近結束,原子彈發明以后,才進入一部分人的深省。原子分裂所發生的力量是非同小可的,以視蒸汽的力量,電流的力量,不知要大出若干倍數。惟其大,所以更難于駕馭控制,大底為了破壞的目的,在制敵人的死命的心情之下,此種控制比較容易,所以原子彈是成功了。但為了建設與人類福利的目的,控制的功夫似乎要困難得多了。淺見者流不斷的以進入原子能新時代相夸耀,把原子能可能產生的種種福利,數說得天花亂。不過沉著的科學家卻不如是其樂觀,即如英國軍事委員會的科學顧問艾里斯教授說,我們可能用原子能來駕駛海洋上的巨輪,但為了保護乘客與船員,所必需一種防范機構一定是笨重得不可想象,甚或根本不可能有此機構。又如生物學家赫胥黎說,原子分裂所發生的種種高度放射作用對于人的健康與遺傳是極度的有害的。這又引起控制與防范的問題了。再如英國奧立芬脫指出制造原子能的廠房一帶所遺留的灰渣會發出種種致命的電子性的『毒氣』,而毒氣所波及的地帶,根本無法防衛,長期的成為無人煙與不毛之地。
也就是這一類的科學家如今正進一步的呼吁著物力的控制,覺得前途控制一有疏虞,文明人類便要瀕于絕境。不錯的,這是一個臨崖勒馬的時候了。不過我們在上文已經指出,問題的癥結不在馬,也不在那勒的動作,而在那作勒的動作的人,如果人本身有問題,臨時不是不想勒、就是根本不會勒,總之,他對自己既作不得主,名義上對物做主,實際上等于被物作了主去,就是,一發而不可收拾。據說,當初英、美、加等國的科學家在新墨西哥試驗場上,等待第一顆原子彈爆發的時候,大家就手捏一把汗,深怕它引起所謂連鎖的反應,一發而無所底止;后來幸而沒有。可見即在謹嚴的科學家手里,物力的控制也不是一件有把握的事,一旦如果掉進希特勒一類的人的手里,殃禍所及,那真是不可想象了。
總之,我們不得不認定人的控制是一切控制的起點,是一切控制的先決條件。人而不知善自控制,在他應付物力的時候,別人想諄諄的勸勉他作妥善的運用,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也認為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不在政治、經濟、社會的種種安排,有如近頃許多作家所論,而在教育。童子在操刀以前,必須先受一番『明』『強』的教育。
, 以上就是對潘光旦的評價(重溫觀察潘光旦對人與物的控制的思考)的內容,下面小編又整理了網友對對潘光旦的評價(重溫觀察潘光旦對人與物的控制的思考)相關的問題解答,希望可以幫到你。
#有獎征文#有沒有一部電影作品你覺得被低估了?
1 行騙天下,又名信用欺詐師。 運勢篇作為行騙天下的一部番外,時長105分鐘,依然非常精彩。 這是一部輕松搞笑的懸疑片,最為懸疑推理劇就好比李狗嗨在律政劇中。
現在的學生比較叛逆,抗挫能力太差,老師該不該管?
感謝邀請: 引導孩子學習成長的行為習慣是家庭教育的核心工作 人生為逐步習得適應群體性社會生活的本領,成長歷程中需要經歷或接受的教育內容多種、多樣,歸結起。
民國最牛的國學大師是誰?
現代教育制度引入中國,也只有120年歷史。之前實施的是科舉制度,雖然在考試科目中增加了少數西學,但不是完整的教育體系。民國的大師耳能熟詳,有誰認真讀過他。
你所在的城市這十年都發生了什么的變化?
在石家莊生活了將近20年,我忘不了最初對她的感覺,“土”,對,就是土得掉渣兒。從名字含有一個“莊”字就感覺她和省會地位不相稱。在我老家,很多村莊的名字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