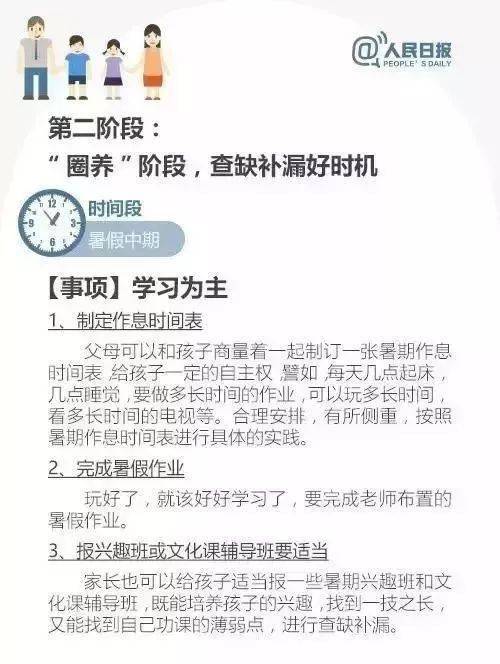(為了兒子,陳燕放棄了戀愛婚姻,做了一個美麗的媽媽。)
這是一個不同一般的腦癱兒童家庭的故事。
5:05 起床

(浩然雖然有6歲,因為腦癱卻像個木頭孩子,不會說話,不會與人交流。)
陳燕起得比太陽早。此時的窗外寂黑一團,只有孤單立在路邊的路燈,為早晨提供僅有光亮。
陳燕悄悄下床、洗漱、準備早餐,以免吵到兒子。她想讓兒子多睡會兒,哪怕只有幾分鐘。因為迎接他們的將是一天的奔波。
6歲的兒子此刻睡得還熟。濃密的睫毛蓋在眼睛上,像女孩子一樣精致的五官鑲嵌在白皙的臉上。陳燕嘆了一口氣。“這么好的孩子,你能看出他跟別的孩子不一樣?”
兒子在兩歲多的時候,被診斷為腦癱。為給兒子治病,陳燕每天帶著兒子在清鎮的家和貴陽的醫院間往返。
“他就是我的命,再難我也要給他治病。”陳燕說。
而這樣的命,是陳燕自己選擇的。2010年,一個夏天的清晨,陳燕騎著自行車去上班。就在即將到達一個轉盤轉彎的路口時,她向右手邊電線桿的草叢里瞥了一眼。
這一眼,幾乎改變了她以后的人生。
沒風,那一瞬間草叢卻動了一下。陳燕好奇,停下車去看個究竟。草叢中,一塊黃底的花布包著一坨東西,她一下子警覺起來,撿一根小木棍輕輕挑開花布,她使勁眨了眨眼,確認自己沒有看錯——那竟然是一個差不多只有男人巴掌大的孩子。
“像個小貓崽兒”,陳燕記得,當時,孩子的臍帶打著節,身上的血還沒有擦干凈,麻繩一樣粗細的小胳膊小腿,幾乎用盡了全身力氣不時的一蹬一蹬。
陳燕警覺的心一下子柔軟下來。她走上前去,小心把布包好,輕輕捧起孩子。這是個男孩。
捧著孩子,她的心砰砰砰直跳。那時她29歲,沒有生過孩子。她不知道該拿這個小家伙怎么辦。她想到了社區。“去問問社區的阿姨,她或許有辦法。”社區阿姨告訴她,應該把孩子送到派出所,派出所說應該送到福利院。
但,陳燕不知道福利院在哪里。
或許是在走出派出所大門的那一刻,又或許是在四處送孩子的路上,陳燕下定決心,“我養他算了。”
陳燕把這看作是冥冥中的安排。那時候,她離了婚,沒有孩子。“每個女人都想當媽。他就是老天爺給我的孩子。”她說。
她把小東西帶回家。這個孩子實在太小了太孱弱了,陳燕一稱,只有3斤多。最開始,她根本不敢碰他,怕稍不注意,就弄斷他的胳膊腿兒。只能請已為人母的姐姐為孩子洗了澡。
她給孩子取名陳浩然。這個名字是一個電視劇里的角色。陳浩然從小在農村長大,后來考上大學,畢業后又回鄉做貢獻。
“我就想我兒以后也考大學。”她滿心歡喜的憧憬。
5:50 出門

(陳燕抱著幾十斤重的兒子下樓梯。)
背起一只黑色的大書包,一手牽著兒子,陳燕出門了。書包大概有10多斤重,里面裝著水、飯、尿不濕以及在醫院做水療項目需要的浴巾衣物等。兒子很乖,起床這么早,沒有哭鬧,一路跟著媽媽。
在收養兒子的前兩年里,陳燕很享受做媽媽的感覺。她給他買小衣服,用嬰兒的襁褓把他裹得溫暖舒適;她沒有奶水,就買奶粉給他喝,這幾乎每月要花掉她一半的工資;她給他唱自己唯一會的一首兒歌,《世上只有媽媽好》,輕輕悠著他入睡。她努力學著去做一個母親。
抱孩子回來沒多久,她就帶孩子去辦了收養手續。在醫院檢查的時候,醫生評估,這個孩子可能是個未足月的早產兒。
為收養兒子,她和戀愛中的男友分了手。然后又跟全家人鬧翻了,除了母親——陳燕唯一的支持者——家里人都覺得,帶著孩子,陳燕這輩子就別想嫁人了。
對于陳燕來說,這些都沒關系,因為她是孩子的媽媽了。盡管眾叛親離,陳燕覺得,她和兒子相依為命的日子也很好。
兒子一天天長大,從小貓崽兒,長成白皙可愛的嬰兒。只有一點似乎不太對勁,孩子太乖了,“幾乎不會哭鬧,即使哭,也是很小很小的聲音。”而且,俗話說,嬰兒“三翻六坐九爬”。她納悶,“我兒兩歲多了咋還不會走也不會說話?”
她帶兒子來貴陽的醫院檢查。醫生告訴她,兒子患有腦癱,可能與兒子是早產兒有關。如果不干預治療,很可能一輩子都不會說話走路思考。
她背著兒子走出就診室,越走越覺得累。走到婦幼保健院門口那長長的臺階上,她終于走不動了,坐在臺階中央嚎啕大哭,嚇得路人都不敢駐足,悲慟得好像全世界只剩下她和兒子。
哭到哭不動了,她想起兒子該吃飯了,又背起兒子去找吃的。走著走著又想哭。“這幾年,把我前面20多年沒流的眼淚都流完了。”
兒子需要治療,可是她沒有錢。2014年,在醫院幫助下,她申請到了殘聯在婦幼保健院設置的、專門為家庭貧困的腦癱兒童免費康復訓練的項目。項目每年進行4個月不間斷的治療。從那時起,她和母親輪流帶著兒子往返清鎮和貴陽。
不幸的是,一年前,母親患糖尿病癱瘓了。她只能一個人帶著孩子上午去貴陽治療,下午靠跑“殘的”掙錢。除了每月400元的低保,跑車掙的錢幾乎是母子二人唯一的收入。兒子沒人照顧,跑車的時候,陳燕就帶著兒子。在兒子還是小嬰兒的時候,陳燕把他放在“殘的”的后備箱里;等到兒子長到后備箱放不下,就讓他坐在后座。
每天,她和兒子要在8點過就趕到醫院,所以常常出門的時候天還沒亮,大街上幾乎空無一人。
路燈下,兒子的身影被拉得老長;而陳燕的影子,則被扯得變了形。陳燕患有糖尿病,為了省錢,她將每天需要打的兩針胰島素,減少到一針。病情無法有效控制,許多并發癥找上了陳燕。半年前,她的一只耳朵聽不見了;兩個月前,她的左腿開始無法伸直,走路一跛一跛。因患病,兒子走路也不利索。她自嘲,“大跛子帶著小跛子。”
從清鎮的家里到貴陽的醫院有30多公里路程。她當然舍不得開自己的“殘的”去。“一個來回加上停車費要幾十元。我哪有那個錢。”
為了省錢,就免不了折騰。她和兒子通常先是開車到距離等車地點最近的一個免費停車場,然后再步行20多分鐘,到高速公路口不遠處,去等開往貴陽的面包車。
一路上有些出租車招呼陳燕去坐,20元一位。陳燕連忙擺擺手,“坐不起,坐這個車,我兒都要算錢。還是10元錢的面包車劃算。”
這一天,陳燕的運氣不錯,剛到了等車地點,就有一輛6點45分出發的面包車。“往常可能要等個一二十分鐘,有時候等半個小時。”
聽說陳燕是帶著孩子去貴陽治腦癱,同車的人都嘆息,“看著這么好的一個娃兒,可惜了。”
陳燕愿意向這樣的陌生人袒露心聲,他們投來的同情里總是夾雜著贊許,能讓她獨自一人苦苦撐的生活,獲得些許安慰。
7:45分 到達貴陽

(為了兒子盡快康復,陳燕習慣了大清早6點,帶著兒子從清鎮奔波到貴陽。)
面包車不能進城,陳燕跟著同車的一位老人在花果園下車。老人和陳燕的目的地在同一個方向,她帶著陳燕一起坐公交車轉車。
早上的公交車,人滿為患。陳燕和兒子擠在人群中,老人看不過去,請身邊有座的乘客讓座,“她的孩子是腦癱,請給讓個座吧。”一位睡眼惺忪的上班族,起身把座位讓了出來。
一路上,老人都在跟陳燕討論孩子該如何帶,如何治病,有沒有一些辦法可以幫到他們母子。
下車的時候,公交車的司機主動給了母子倆一個“特權”。“太難得擠,你們從前門下吧。”
陳燕一陣感激,連聲說著謝謝拖著兒子下車。還沒走出車站,一位年輕的姑娘沖過來,塞給陳燕100元錢。可能是在公交車上聽見陳燕帶著腦癱的兒子不容易,姑娘滿眼淚花,“拿著吧,好好帶這個娃娃,你們會好的。”
陳燕對這突如其來的善意不知所措,哭著“撲通”一下跪在大街上,“我真不知道說什么好,這么多錢,謝謝謝謝。”
姑娘扶起陳燕,拍了拍她的肩膀,哭著轉身消失在人群里。
陳燕牽著兒子抽泣著向前走。一位老人領著一個大約兩歲的小女孩兒,過來搭訕。“你們去婦幼保健院做康復治療?”
陳燕點點頭,“我娃娃腦癱。”
“我們也是去做康復治療。”老人說。
陳燕抹了一把眼淚,有些詫異,“這小娃娃看起挺好的啊。是什么病?”
老人沉默了一會兒,然后拉長音回答“自閉癥。”語氣里全是嘆息和悲涼。
一時間,陳燕和老人都沒有再說話。,老人走遠了,她才嘆了口氣,“各家有各家的難。”
8:20 治療

(浩然接受康復治療。)
陳燕和兒子到醫院的時候,只有三個家庭在康復訓練中心等著。她找到一個位置,等著醫生來為兒子上儀器。
等待間隙,她拿出剛剛買的糯米飯喂兒子。對于兒子來說,這是一頓奢侈的早餐。
通常,陳燕出門之前都會準備好在醫院吃的早餐和午餐,用一個不銹鋼飯盒裝起來。所謂的早午餐,有時候是炒飯,有時候是稀粥或者面條,每天只有一樣東西。甚至,如果當天帶的飯在醫院沒有吃完,陳燕還會帶回家來當晚餐。“天天在外面買飯買不起。”
而今天這頓糯米飯不一樣。在醫院門口,兒子看到了糯米飯的攤攤就不走了,眼巴巴的喊著“媽媽,媽媽”,意思想要吃。
陳燕大喜,“他現在會要東西了。”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剛剛接受治療的時候,兒子雖然已經將近3歲了,可是就像個小木頭娃娃,不會說話,不會走路,不會跟人交流,“眼睛看到哪里都是直勾勾的。”

(浩然平時很安靜,眼睛里似乎有很多話卻說不出來。)
那時候陳燕一度絕望,“這娃娃還能治好嗎?”讓她沒想到的是,兒子的治療效果非常好。貴州省婦幼保健院兒童醫院康復科護士長蒙家紡介紹,陳浩然的治療分為理療、水療、認知訓練、運動訓練等,每天要進行大概5個小時。“陳浩然的治療效果應該說是很不錯的。第一年的治療結束的時候,這個孩子就可以扶著墻慢慢走了。剛進來的時候,他每天還是他媽媽滿頭大汗的背著來。”她說。
這也是陳燕堅持的動力,“我兒子一定能治好。”今年9月初,治療剛剛開始的一天。陳燕帶著兒子做完水療,給他穿好衣服之后,就去收拾書包。收拾好一轉身,陳燕慌了,兒子不見了。
她扔下書包就往外跑。跑到走廊上,他看見兒子正在獨自吃力的向前走。為了保持平衡,兒子雙手張開,身子一拱一拱的向前走,像一只小鴨子。望著兒子的吃力的背影,陳燕哭了,“終于會走了。我的寶貝太厲害了。”
現在,雖然平衡感還差一些,兒子卻已經能獨自走的很順暢,甚至可以跑。有時候,兒子一跑起來,陳燕因為腳跛根本追不上。“為了抓住他,我就跟‘躲多喵咪’。”陳燕說,她一躲起來,兒子就會來找她。

(為了兒子,陳燕不知下跪多少回。)
而這一天,兒子又開始知道要東西了。“這說明他長心眼了啊,他一點也不傻。以前哪有這樣的時候。”陳燕樂呵呵的為兒子買了一盒糯米飯。
兒子要吃東西,或者累了不想走的時候,就會喊“媽媽,媽媽”。這是在差不多一年前學會的。那時候,陳燕去找了些土方子給兒子熬藥。藥難喝,兒子每次都抗拒。為了哄兒子喝藥,陳燕告訴兒子,“寶貝乖,喝了藥就會喊媽媽了。”
沒想到,就在一次喂藥的“斗爭”中,兒子在掙扎中叫出了“媽,媽媽”。
兒子的吐字并不清晰,但是這兩個字足以擊中陳燕。她不顧一切做了這個與她沒有血緣關系的孩子五年的媽媽。他不會吃飯,她喂他;他不會走路,她背他。他不會說話,她就說給他聽。
在陳燕終于聽到兒子喊出媽媽的那一瞬,她抱著兒子嗚嗚哭了起來,“這么多年終于會喊媽媽了。”她記得,那一天,她哭了很久,因為有太多的委屈需要釋放。
13:35 回家
做完一天的項目,已經到了下午。5個小時的治療,陳燕比兒子累。兒子在做理療的時候可以休息,陳燕卻不能,兒子總要賴著她抱。
更糟糕的是,她吃飯之前忘記了打胰島素,這讓她渾身酸軟,“一點力氣沒有”。她想找個地方躺下來休息下,可時間不允許,她還急著早點回去跑車。

(陳燕剛剛自己注射完胰島素,又要去照顧孩子。)
只是喝了口水,陳燕就牽起兒子往車站走。她太累了,步子明顯沒有來時候走得快。回來時背的書包顯得更沉了,像這沉重的生活,仿佛隨時可以將她壓垮。
的確有這樣的時候,陳燕差點就挺不過去。2015年,她被查出了糖尿病,檢查時的血糖高達23點幾。醫生告訴她,這么嚴重的糖尿病,如果不及時治療,隨時有生命危險。
陳燕犯了難,兒子需要24小時不離人的照顧,如果自己住院,兒子怎么辦?她把能求的人在腦子里過了一遍,發現沒有人可以托付。最終,她只能將兒子送到兒童福利院。
她給兒子買了一套新棉絮,四套新衣服,把這當作生離死別,還寫了“遺書”。“如果我治好了,我就來接走她。如果沒治好,死了,希望他以后能到我墳上燒柱香。”
從與兒子分別開始,她就哭,在醫院治病的時候,她也哭。期間她偷偷跑到福利院去看兒子,隔著玻璃,兒子看見他,就摟著福利院阿姨的脖子哇哇大哭。她看見了,哭得更厲害。
陳燕覺得命運還是眷顧她。治療了一個多月,陳燕的血糖降了下來,盡管還有比較嚴重的糖尿病,卻已經不至于威脅生命。
她把兒子從福利院接出來,母子終于團聚。從那時候起,她再次堅定了信念,“他的命就是我的命,我要帶著他好好活。”
她每天只打一針胰島素,如果覺得不舒服,就吃一顆口香糖。“這樣我也能堅持。我聾了瘸了都沒關系,只要我兒能好,我瘸一輩子都可以。”
在回清鎮的面包車上,陳燕和兒子相偎著睡著了。車子嘈雜顛簸,也沒吵醒他們。也許,這解乏的小憩會有美夢。
下了車,陳燕牽著兒子去取車。她走一段休息一下。花了將近半個小時,才走到早上停車的地方。
她決定這天下午還是不去跑車了。“真的太累了。”她盤算著,第二天是周六,不用去醫院,可以早點起來跑車,“賺回今天的損失。”
15點40分,母子二人終于到家樓下了。陳燕拽著兒子爬樓梯。她弓著背壓低重心,以便更好使力。大書包的肩帶卻總是在她弓背的時候,一次次往下滑,她就用力一次次把肩帶拉回原處。就像一直以來,她一次次頂下她生活里的重壓。
走到了家門口,她發現一只飲料瓶。這樣的瓶子只能賣1毛錢,人們通常會順手丟棄。但是對于陳燕來說,1毛錢也是希望。她俯身撿起瓶子,扔到自己家的陽臺,那里堆了不少這樣的空瓶子。在沒有太陽的這個下午,它們好像仍然在陳燕的生活里閃著光。

(文/本報記者 李盈 圖/本報記者 劉婷婷)
轉載自頭條號:貴州都市報